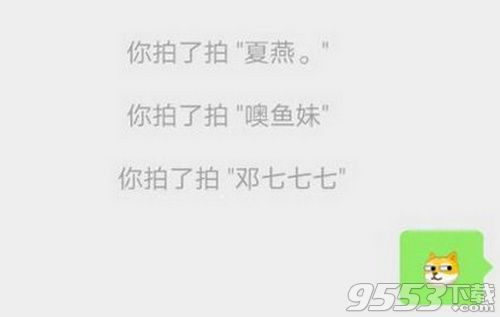消息丨诗人李瑾推出《观影录——我们如何逃离自己的身体》
由南方出版社出版的《观影录——我们如何逃离自己的身体》,是作家、诗人李瑾新近推出的哲思类影评著作,本书和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谭诗录》同为姊妹篇,两本著作都以电影或诗歌为媒介,探讨人的“存在”这一终极性哲学和伦理命题。《观影录》依旧是“地铁诗人”李瑾乘坐地铁玄思的产物,故而收录其中的文章短小精悍,好读耐读,收录其中的短章一文一主题,一文一问题,通过探讨电影的不同侧面,阐释电影的生发、运转和价值问题,即通过分析电影是什么、人为什么需要电影这类“元问题”,摸索“人”及其存在的真相。《观影录》除导言和跋之外,分为正文五十篇和三个附录。作为核心的正文部分,李瑾从五十个“问题”角度诸如时间、困境、死亡、正义、自由、启蒙、现代性、视觉、空闲、消费、偶像、身体、身份、色情、反派等,以基本相同的篇幅探讨了电影的不同侧面。附录一评论了《大独裁者》《摔跤吧,爸爸》等中外十部经典电影,录二点评了《吾栖之肤》《决战犹马镇》等二十五部不同类型的电影,附录三收录了李瑾和文化学者安歌的对话。现将对话刊出,以飨读者。
电影是一种普遍的忧伤
双方:安歌 李瑾
时间:2020—12—4
安歌:我觉得跨度或者说转变有些大。上次还是就《谭诗录》进行对谈,畅论诗歌现代性诸问题,现在邀请我讨论电影。虽然我也是电影的自愿性“俘虏”,但还是忍不住想问,你为什么选择把电影当作话题?
李瑾:其实并不突兀,在我的视野中,诗歌和电影隶属于人的内在,同是人的规定性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它们和自我或人的本性是相互涵养和呈现的。刨除诗歌而言,我们都算是电影一代,虽然电影已不是生活中的主要娱乐方式了,但在视觉文化工业时代,电影依然是最高端和最深邃的“眼神”,因为按照一个经典的说法:“电影是一种思想,其作品就是现实。”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电影其实是在谈论生活和我们自身。我的核心观点是,电影中的角色,无论正面的、负面的还是毫不起眼的,包括种种熟悉的、陌生的乃至不可能存在的场景,都是我们正在经历着的生命、生活的投射——如果说负面的形象对应着潜存的“恶”,不可能的则更为珍贵:它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的生命形式、生活方式如此丰富,遗憾的是我们只选择了其中一种,而且过得并不如意。
安歌:我同意你的说法,电影并不单纯是一种娱乐方式,不能只从器物或工具层面去观看观察观测电影,因为它提供了人和生活的种种面相和面向,即见证了人的存在。法国哲学家阿兰 巴迪欧的另一个著名身份是影评家,他曾经说:“康德拉层这样评价小说:它的使命是给可见的世界以公道,而这也正是电影的使命!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电影:在烂片中,人的呈现被糟蹋了,它在那里毫无作用。而在一部好电影中,哪怕只有两秒钟,这种存在都是可见的。”
李瑾:他的说法符合我这本书的使命。我写《观影录》和《谭诗录》的目的其实一样,即不能直观地理解我们喜欢的东西。假如我们只沉浸在枪火、美色和各种剧情及其翻转中,将会忽略电影最伟大的价值——在我的观念中,电影是人反复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行动。意思很明显,人受制于社会提供的他者和规训,故而从来都不是完全的、自然的,即人无法正确、绝对的理解自己和所处的世界,而电影通过提供种种镜头、角色,让我们看到了驳杂的生命河世界。这个意义上,电影是启蒙的产物,而本身亦是一种启蒙方式,它就是个人在发现主体性过程中诞生的。
安歌:你的这个观察是中肯的,我还记得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有这么一段演讲:“生活的道路可以是自由的、美丽的,只可惜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发展了速度,但是我们隔离了自己。机器是应当创造财富的,但它们反而给我们带来了穷困。我们有了知识,反而看破一切;我们学得聪明乖巧了,反而变得冷酷无情了。我们头脑用得太多了,感情用得太少了。我们更需要的不是机器,而是人性。”《大独裁者》的主题既是批判,也是发现,而这恰恰是对人的启蒙。
李瑾:没有办法,现代生活已经完成了对人的吞噬,如果说之前被机械化了,现在则被信息化了:我们被编码处理得无限大又无限小,不是我们的生活细致、便捷了,而是我们自身被粉碎得更细致、运用得更便捷了。你看,银幕本身就和窗口一样,在这个窗口中,我们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命运。现在,电视、Pad、手机和高楼大厦都窗口一般朝人间洞开,这个状态既虚幻又真实,形形色色的人和命运呈现出高度的一致。如此一来,意味着人的同质化,这是信息社会带给我们的后果。
安歌:我知道你的意思不是逆信息化,即对现代性抱有一种绝对敌意,只不过是想说明人的异化和丧失。电影又何尝不是如此?
李瑾:是的,既然电影是人反复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行动,电影和人的沦陷是同等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我们说到电影,就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作大片。大片是什么?它是商业化和信息化合谋而成的产物。如果说传统电影/胶片电影是主观性很强的艺术创作,数码电影则是手工性很强的技术操作,即只需在狭小的、密闭空间比如摄影棚、计算机中就可以完成一部视音效果非常震撼的影片。某种意义上,电影拍摄不需要表演,只需要表情和软件,通过大量电脑制图就可以完成“拍摄”——倒不如用设计或制造更合适一些。
安歌:由此带来的最大的麻烦是,观众亦即我们被大片化了,也就是类型化了。恰如《观影录》中所说:“我们被大片殖民了,被改造成为大片人,而这些都是基于电影票房这一商业需要。电影以赤裸裸的消费主义改造了我们的价值观,这是一种最便宜和最便利的统治。”当然,信息化引起的大片化是表面问题,深层次上则是对叙事以及生活模式的改变,电影中的“价值”“规则”以人类代言人自居,而我们则被统一为追求娱乐和感官刺激的物质人。
李瑾:这样一来,我们曾一度追逐且尚未完全实现的个体生命、自由、权利之类的观念再度迷失。当我们将启蒙定义为人的自我发现和拯救,意味着其和电影“同体”了,它们共同的任务都是重新发现人。通常意义上,人们走进电影院是为了休闲娱乐,殊不知所谓休闲娱乐不过是消费亦即社会生产的必要环节,如此我们将悲观地发现,假如我们仅仅局限于消费式地看电影,希望自电影中寻找安慰、按摩和安逸,无异于再次被资本和消费统辖和治理了。故而,一部好的电影必须饱含冲突和矛盾,因为种种不舒适会刺激个我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当我们观看电影时,必须注意剪辑和视点选择中的伦理行为/后果,能指证、修正我们的存在的即可以看下去,假如仅仅让我们觉得快乐,就得直接放弃了:奉承、迎合感官之欲,只会让人加快坠落。按照我的理解,绝大多数电影都不值得观看。
安歌:吊诡的是,休闲娱乐对应着人本主义和消费文化,这恰恰是启蒙赋予的,如今又成了启蒙的对象——当然,说人本主义和消费文化是启蒙赋予的并不完全正确,资本主义带来了启蒙,两者互为对象。这种吊诡一方面说明启蒙一直在路上,一方面说明批判固然是必然的,但不必过分悲欢,人永远在自己身体不停地进步,和电影一样,人和技术相互塑造。你说绝大部分电影都不值得看,但好像你是电影的忠实粉丝。
李瑾:因为忠实,所以背叛。我确实看了很多电影,但相对于生产数量而言不过九牛一毛。这里,必须老实交代,我也喜欢商业巨制,更喜欢动作、警匪、悬疑、恐怖这类片子,相反,对文艺片一直非常抗拒。但是,我说过了,如果电影只是让人舒服不如去泡澡、晒太阳,电影如果不能刺痛一个人它注定是失败的。我还记得在2000年在地质礼堂看过来京后的唯一一场通宵,三部动作片,一部《安娜 卡列尼娜》。当时,看《安娜 卡列尼娜》时睡着了,当时我确实把它当作中场休息,但文艺片的魅力就在于你没怎么看却忘不掉,如今那三部影片名字忘记了,但安娜决心“不让你折磨我了”,坦然让呼啸而过的火车结束了自己无望的爱情和生命的形象一直留在脑海——这无疑也印证了电影和觉醒是同义的。
安歌:《观影录》附录部分三十五部电影确实泄露了你内心的私密即个人的倾向和钟爱。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无论你看什么片子都津津有味,并试图琢磨些什么出来。恕我直言,你点评的一些影片大部分在严格的影评家看来都不入流。
李瑾:电影既然是人反复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行动,显然和内在个我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因为个我是唯一的、孤独的,他必须对身体内部的那个生命负责,故而可以选择符合自己的方式。我当然知道这些影片并不怎么宏大,但必须对时间这个最大的他者有所交代,因此无论看什么电影我都保持思索,哪怕一两句皮毛之得,也算是和自我/时间对话了——众生皆苦,唯我自渡,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某种意义上也是超越。不过,需要警惕的是,要对电影中的“真理”“规则”亦即某种神话保持距离,喜欢本身就意味着成瘾性或者说规训。我的做法是,看电影不跟市场,不跟宣传,不跟评分,有时一部电影公映了十几二十年才会去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从来不看奥斯卡最佳影片,这么极端其实是刻意为之而终于无意,我最担心的是别人的评价影响了我。《百万英镑宝贝》获得第77届奥斯卡四项大奖,看名字我还以为讲穷小子发横财的故事,2005年赴美途中百无聊赖,点开机载影院看了,才知道是讲拳击手的,这部电影好就好在教练法兰基和学生麦琪借助拳击亦即对方重新发现了自己——电影永远在讲人的自我寻找,无论美还是恶。
安歌:故而电影是一个人的事业,而且是深夜事业,我的意思是说只适合一个人安静地看,它不是晚会,不需要掌声,只需要内心和真实的眼泪——我怀疑咱们把电影说重了,因为电影并不否认大众,相反,它需要大众/票房的支撑,否则它就和诗歌一样了。
李瑾:电影既是个人的,也是大众的——这并不矛盾,不能简单地将这个个人理解为精英,否则会造成所谓雅俗的二元对立。电影和启蒙一样显然是聚焦大众的,同时,当它作为一种“产品”呈现出来,只有进入流通才能创造价值,并对创作者的付出——和生命同质的工作时间——进行衡估。必须要确认的是,大众是有个人组成的,在任何时候,大众只是一个化约性甚至乌托邦概念,即一说到大众本身就意味着解体和分散(分层)。这就是说,电影虽然是拍给大众的,其实是拍给个人的,个人的观影体验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只有少数个人能通过电影发现自己的不能和可能,发现自己的善和恶,发现自己的边缘和困境——只有这样的个人才能通过电影找到自己,或者看到自己其实是个未完成的人。
安歌:这样说来,电影是不是不好玩了?
李瑾:当然好玩了,你可以放纵也可以沉思,同时可以选择被几个不明所以的人挠几下——这已是当下搞笑片的通病。只是我觉得最深层次的好玩是发现个我的更多维度和生活的更多可能。尽管我已无力做到,但我发现了。我常常和身边人说起,人类最深邃和最广泛的爱都是爱自己,无论你承不承认,只有你守在肉体里陪伴自己一生,这是不得不接受的宿命。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电影,会发现电影是一种爱的行动,它是对个我的补充和阐释,故而阿兰 巴迪欧才会说:“电影捕获的是目的是识别身份认同的故事。”这已在说明,无论人还是爱都容易迷失,或沉浸在幻觉里。
安歌:我理解了你为什么采取玄想的方式谈论电影了,电影和人被你同义而语了。也就是说,你从各个维度阐释电影无非想表明人不是同一的、同质的而是自然的、自由的,但由于被资本和消费统治,人会丧失自己的主体性甚至尚不自觉,你期望通过宏观讨论深入解析这些问题。
李瑾:是的,这就是引用电影情节、对话和相关讨论却不标明出处的原因,我希望读者和我一样能够从一部电影中跳出来,如果只是为看而看或者陷入某部片子之中,我们将进入新的困境。按照我的理解,痴迷或陷溺于任何一个事物都会自投罗网,至少坐井观天。只有跳出来旁观它,才会察觉到自己的此在和事物的虚妄。不得不说,现代性赋予了我们很多,也剥夺了我们很多——如果连看电影即体验自己存在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就是不存在的,换种说法是这种存在毫无意义,因为我们都被程式化、工具化了。这个层面上,电影表达的或其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忧伤,一种人类自我缅怀的忧伤:人永源在追寻自己的路上,但看到的只是霎那间出现的光影。
李瑾山东沂南人,汉语言文学学士、新闻学(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有作品在《人民文学》《诗刊》等百家报刊发表,出版“三释”“二录”“一裁”(《未见君子——论语释义》《新子之国——孟子释义》《其名自号——山海经释义》《谭诗录——实然非实然之间》《观影录——我们如何逃离自己的身体》《纸别裁》),以及诗集《倾听巴赫和他内心的雪崩》《落雪,第一日》《黄昏,闭上了眼》《人间帖》《孤岛》、故事集《地衣——李村寻人启事》、儿童文学作品《没有胳肢窝可怎么生活啊》等,曾获得东丽文学大奖、李杜诗歌奖、海燕诗歌奖、中国诗歌网年度十佳诗人、《中国诗人》年度成就奖、华西都市报·名人堂年度十佳诗人和名人堂年度十佳诗集等奖项。
总编辑:邢越
文學陕軍新媒体联盟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