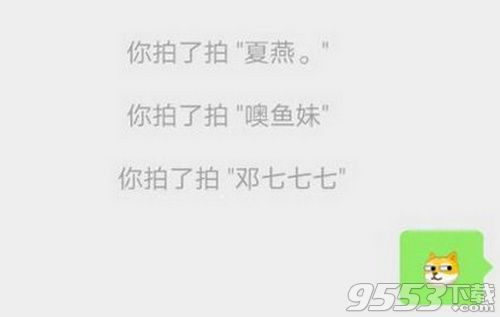这部古怪异常的电影,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泰国导演阿彼察邦的新片《记忆》,绝对是部让人“难以下咽”的电影,但该片却在去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拿到了评审团奖。
此前,阿彼察邦凭借其“更难下咽”的《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拿到了2010年的金棕榈大奖。
可以说,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这位泰国导演,不管是放到亚洲电影界,还是世界影坛,都是一位在影像上独具创新的先锋者。其电影佶屈聱牙的程度与其丰富深刻的内涵往往构成正比,越是让人一头雾水的影片,越是探索人类心灵的未垦边界。
从这个程度上来说,《记忆》绝对是今年不可错过的一部杰作。
女主角杰西卡为了看望患病的姐姐,来到波哥大,没想到姐姐却在病房向她透露出颇为神秘的患病原因。
在姐姐的描述中,自己的这些不适症状,都是在一场梦境之后发生的。梦里,她看到一只身负重伤的狗,但她却冷眼旁观,并没有对它施救。所以姐姐认为,自己是被梦中之狗下了诅咒。
可几天之后,当杰西卡和姐姐在饭桌上再次相遇时,她却从姐姐的口中获知,后者是因为热带雨林里的原始居民的诅咒,才患上怪病。真相到底如何?姐妹二人貌似并不愿深究。
但杰西卡在波哥大这座城市中,开始不断遭遇“幻听病症”。
从一开始,她因为脑中的轻微幻听而在凌晨惊醒,无法入睡,到在大街上过马路时突然听到更大的声响,甚至在和姐姐一家人聊天的过程中,脑内不断响起猛烈未知的撞击声。杰西卡的这一连串遭遇,毫无征兆,也无法查出缘由。
她试图找到一位音效师赫尔南,请他根据自己的描述,模拟出脑中的“幻听”声响。可当杰西卡再次寻找赫尔南时,和后者同一栋大楼的几位音效师声称此人压根不存在。
诡异的事件在影片后半段不断发酵,当杰西卡来到一处偏远的小镇乡下,和一位农夫寒暄闲聊时,竟得知后者的名字也叫赫尔南。这位中年赫尔南声称一生从未出过小镇,在他得知杰西卡无法入睡,频频做梦后,他表示自己一旦睡着,不会发生任何事,连梦境都不会产生。
而就在中年赫尔南当着杰西卡的面“表演”睡觉时,杰西卡惊奇地发现,赫尔南不但不会做梦,更是睁着眼睛毫无动静,连呼吸都没有。就在杰西卡以为赫尔南已经死去时,后者却逐渐苏醒,恢复意识。
最后,杰西卡在这位神秘男人的居所中,“获取”了他所经历过的一生记忆,并且能够清晰地感知到此处的过往种种。
影片除了展现发生在杰西卡身上的一系列神秘现象,更是在全片插入各种语焉不详的片段。比如杰西卡参观考古实验室时,在研究员的引导下抚摸着6000多年前一颗女性的头颅;亦或者是哥伦比亚的一处隧道修建现场,几位考古人员对于所挖掘出的骸骨进行清理。
很多人看完本片之后,都不禁会问,这到底讲述了怎样一个故事,或者表达了什么主题?为什么杰西卡的脑中总有幻听?影片最后她能“获取”记忆因何而起?
这一切的疑问,其实并不能简单地用故事梳理和主题归纳来敷衍了事。对于《记忆》这样的艺术片,我们能领悟到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意旨。
其实,《记忆》并不是一部以叙事为导向的影片,单是这样一点,就让它区别于绝大多数的电影。这类影片在国内并不多见,但是近几年来,已经有不少年轻的导演开始尝试此类影片的创作。比如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仇晟的《郊区的鸟》。
以叙事为导向的电影,基本都是通过讲述一则故事的起承转折,来形成一种确定性的主题表达和价值态度。比如《你好,李焕英》通过讲述贾玲穿越回过去,在和年轻母亲张小斐的相处中,对母爱进行重新建构,对母亲做出重新认识;或者如《扬名立万》那样,通过推理一桩室内悬疑案件,让一群电影人经受重重考验,并最终达成对正义的追求。
但《记忆》不是这样的,影片中的桥段和场景并没有在因果逻辑上形成必要关系。桥段只不过是导演对于生活切面的某种观察,而场景只是一种符号化的嵌入。所以,你可能会一头雾水,不知道这是一则怎样的故事,也会心生烦闷,在看完电影之后,感觉没有获得任何价值观上的贴合或反驳。
在阿彼察邦的电影中,他永远让人物所处的空间变得虚幻且奇妙,有种超现实的怪味。
比如在《热带疾病》中,影片的前半段讲述了一对男同之间的恋爱,而到后半段峰回路转,两个人成为宗教寓言里的化身,一个是猎虎之人,一个是装着僧人灵魂的虎精。
到了后来的《恋爱症候群》,看似是在讲述一个女医生和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但实际上是通过影片前后的景观对照,表现时空巨变下人类关系的恒常和怪异。
即使在《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这部明确让鬼魂、鬼猴出现的奇幻片里,也并没有烂俗地讲述一则泰国式的“聊斋故事”,而是为我们展现出人类对于死亡和灵魂的复杂态度。
但阿彼察邦的影片,又不是在走恐怖惊悚片的路数,他对于奇幻质感的营造,往往来自于对日常生活的另类观察。
在《记忆》开始不久,就出现一段长镜头画面,停车场的数辆轿车突然响起了警报,此起彼伏。这段看似聒噪的场景,却在阿彼察邦的调度下,显示出另一重况味,你会随着轿车们的“喊叫”,感觉它们是在聊天交流,宛如具有智慧生命一般。
或者是杰西卡在大马路上突然听到一声炸裂声,她本以为是自己的幻听,可没想到与此同时,一辆公交车突然爆胎。不仅如此,一位陌生男人在听到这声巨响之后,下意识地趴下身子,宛如是在躲避枪击。看似不起眼的桥段,被阿彼察邦拍出了三层味道,指向三个不同的方向。
即使是高潮部分,杰西卡和中年赫尔南交谈过程中,后者入睡之后宛如死去一般,也显出超现实的况味。镜头从赫尔南双脚上的苍蝇,切到他双目睁开的面孔,你会在诧异之余,感受到生与死的奇妙切换。生可以体悟到死亡的寂静,而死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生。
阿彼察邦电影的魅力,就在于这种对于现实和超现实的奇妙转换。他总能在最接地气的生活画面中,找到一种超现实的表达方式,但又抛却了虚假造作的特效,以镜头的巧妙切换、画面内的场面调度,试图让我们寒颤乍起,体验到现实中也不乏空灵独特的诗意。
而在《记忆》这部新片中,阿彼察邦更是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剔除抛开,让几位主角宛如僵尸一般,对各种奇幻现象做出反应。这也难怪阿彼察邦在采访中,屡次提到1943年雅克·特纳的那部《与僵尸同行》。即使有蒂尔达·斯文顿这样的顶级演员,阿彼察邦依然想要她成为自己意念操纵下的傀儡。
所以,你会发现,片中的杰西卡像是着了魔一般,在波哥大这座城市的各处地方游荡,参观城市中的现代艺术展,也观看各种远古和现代的物件。
阿彼察邦在这部电影中建立了一种穿越古今、打通生死的活络感。杰西卡这个角色像是一个脱变中的人,她对于人类之前的种种开始怀疑和否定,而对于神秘未知的时空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你很难说,她类似《超体》中的斯嘉丽·约翰逊,是一种大脑物质层面的超越,但她确实在各种怪诞的现实变化中,进入到感知古今的领域。
《记忆》这部电影的独特价值或许在于,它让我们认识到,电影并不只是一种演绎故事的影像载体,它也可以通过饶有趣味的景观构造,探索一种奇妙的超现实之境。
花无宴
标签: 这部古怪异常的电影 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